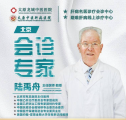[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本篇文章2462字,读完约6分钟
麦浪滚滚,金光闪闪,又是一个丰收年。其实,在小麦收割过程中,捡麦穗,也就是捡麦穗,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项艰苦的、象征性的农业劳动。
是的,捡麦穗是农耕文明的标志。就像法国画家米勒在1857年创作的《拾荒者》一样,它反映了欧洲工业文明之前农民的生活场景。此后,它几乎成为西方艺术史中的一个共同主题。继米勒之后,法国的里昂·莱尔提和朱尔斯·布雷顿、英国的阿瑟·休斯、梵高等著名画家都曾以此为主题传世。这些作品一旦传到东方,就被长期沉浸在农耕文明和中国文化中的具有审美经验的中国人所接受和感动。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摘麦穗确实是农耕文明的一大文艺主题,也是贫苦农民在麦收季节艰难的耕作习惯和古老的习俗。从我国商周文字记载来看,有捡麦穗的记载。《诗经·潇雅大田》是当时的一首农事诗。这首诗的第三章,重点讲述了麦田里捡拾麦穗的场景:麦田里,有的人来不及收割,有的人割完还没完全捆好,有的人捆完还在搬运的过程中摔倒,还有的人匍匐着收不到,都成了拾穗人的收获。自先秦以来,摘穗可能成为小麦生产过程中一种独特的耕作活动,尤其是在小麦收获时期。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所以农耕社会必然会出现贫富差距。因此,在小麦产区捡麦穗成为贫困家庭养活自己的一种特殊方式,允许他人进入自己的田地捡麦穗也是农耕文明中的一种善意和善意。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uploads/diyimg/bk0psgfq3sxgznr5bj8og54sgakb89.png)
据说我奶奶曾经是捡麦穗的“专业户”。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什么程度,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那时候我们家很穷,父母都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就是给当地的商人当学徒,每个人当时都不堪重负。爷爷和奶奶被留在家里。也可能是他们年纪大了,或者爷爷是个很好的说服者,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他离家半年甚至更久,传道授业,劝善讲孝道,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支持他。其实我们家住的是四合院,简单但是比较精致。据说祖辈的祖先曾经被接纳进贡。小时候,我家北门上方挂着一块木牌匾。后来可能是家庭生活的衰落。在我爷爷那一代,因为兄弟们都赌过,抽过烟,家里就剩几亩薄地了。在这种情况下,奶奶自己去捡麦穗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uploads/diyimg/f5j03tae24plqtb3b64n743wzb0fie.png)
奶奶捡麦穗,是从别人的麦田里收割后开始的。每天早起贪吃,白天捡一天,晚上打出去,用簸箕簸十几斤。当时,农业完全依赖于天气。在黄土高原,土地缺水缺肥,农作物一年只种一次。从小麦收获到秋分,再播冬小麦,还有两三个月的土地休眠期。在此期间,奶奶的日常工作是捡麦穗,这是一项特殊的农活。每天从十几斤到几斤;从几斤到一两斤;从一斤到一碗,一碗大概一斤;后来是一天一个茶碗,一个茶碗大概半斤;后来就只是每天一个酒盅。直到农民开始种地播种,这种耕作才告一段落。一年后,据说可以捡一瓮,大概300斤左右。再加上自己地里的一些小收获和一些“瓜菜”,勉强够全家人糊口。现在回想起来,结合我的文化艺术经历,无论是我对米勒《拾穗人》的欣赏,还是我对捡麦的认知,真正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在我的脑海里,我奶奶那幅看不见的《拾穗人》油画。这幅画,虽然别人看不见,但对我来说是最生动、最深刻、最感人的梦。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uploads/diyimg/vlqkz0rr9g4pi7xuq0v7lsn1addur6.png)
其实在北方,在农村,在小麦产区,大家都经历过这种农耕活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方式不同而已。在农村集体生产时期,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还是农村小学生组织起来支农。小麦收割时,大人在前面割,小学生在后面捡。或者生产队集体收割小麦,然后组织成员重新捡拾。这叫高产好收成,或者说勤俭节约,粮食回笼仓库。小时候基本上每年都参加捡麦穗的工作,直到能直接参加割麦队。但是孩子捡麦穗,玩才是主题。在捡麦穗的单调持续很久之前,孩子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看白云,扑蝴蝶,捉虫子,追兔子,玩累了坐在田里的柿子树下乘凉。那时候没有生活压力,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理性的自我意识。听完夏虫的歌声,我甚至很快就梦到周公了。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uploads/diyimg/5hryp96quowzledq8vfj0eqdfw4d3j.png)
我也听过我的孩子在农村捡麦穗的故事。那是90年代,孩子和父母住在农村,但那时候已经承包了合作化,分田到户了。但那时候农村还有小学。小麦收获期间,学校放假,让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去捡小麦,有任务。每个孩子都要给学校交几斤小麦,说是勤工俭学。那时候孩子七八岁,娇生惯养,去地里捡麦子,一天捡不了多少。他们被老师的任务所迫,忍不住捡起来。有一天,两个孩子在田里玩了一下午,捡了起来,但是没找到多少,就要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了一捆从马车上掉下来的小麦,但是开马车的人没有发现。两个孩子大喜过望,就把一捆麦穗分成几捆,连同捡回来的一起,边玩边分别背在背上。回到家,我高兴地向奶奶汇报了我的收获。奶奶第一眼就说你带回来的喜鹊不够大,都丢了。难得是孩子的一次经历。孩子捡麦穗纯粹是一种游戏。捡了一个星期也没打到几斤,离老师的要求还差得远。开学时,奶奶根据学校的数量要求,在家里挖了一些现成的小麦,孩子们高兴地交给了学校。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uploads/diyimg/e2e4uti8kump558bypfjanyfpcracq.png)
现在基本没有捡麦穗这种专业的农活了。农业机械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抛弃了这种耕作方式。是的,时代变了。有些事情是你无法想象改变的。每年回到乡下老家,尤其是秋天,看到田野里柿子树挂满了小红灯笼。以前是农村珍贵的林果经济作物,好吃充饥,可以加工卖钱。但现在都快熟软了,却没人摘。经过走访询问,我们知道农民现在追求的是劳动价值。柿子只有加工成干柿子才能出售,干柿子的加工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在晴天反复干燥。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被雨水损坏,都是浪费。即使在天气好的时候,如果不是专业户加工,它的价格和效益也远不如打工的。在农村,别说有自己的产业,就是100块钱给别人打工一天,20天都是有保障的大金额,而加工柿饼几乎不能保证这么大的收入。就像捡麦穗一样,由于机械化的普及,收割机收割后留下的麦穗并不多。另外,现在农村都是工业化生产,大家都忙着自己的工作。即使有剩余劳动力,他们也出去打工,甚至孩子被送到镇上或县里上学,那里有闲人和空闲时间去捡麦穗。关键是一天捡麦穗的收入远远少于给自己家里打工或者给别人打工的收入。唉,时光流逝,捡麦穗成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uploads/diyimg/ougjdx9i2xq1wj4rln6tvt1ysykm42.png)
捡麦穗成了记忆中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一曲留存在诗经里的悲歌,一曲伟大的世界性乡愁。(作者吴)
标题:[文化]想起麦收拾穗时
地址:http://www.huarenwang.vip/new/20181024/11.html
免责声明:山西时报网是一个向世界华人提供山西省本地资讯的门户网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山西新闻网将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