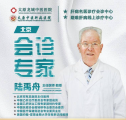[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
本篇文章3261字,读完约8分钟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上。小时候听到《在高高的兴安岭上》这首歌,心里想,谁来写一首《在高高的太行山上》?我爱我的太行山,就像兴安盟的人民热爱他们的兴安盟一样。
谁也不否认太行山雄伟险峻,自然风光秀丽。但由于交通障碍,产品不佳,按照当时的人文指标来看,并不是一个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村民们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深沟里,逐渐形成了相对封闭、停滞的小环境。在漫长的梦想岁月里,他们发酵发展了很多“文化”。这些文化就像地层深处的化石一样,弥足珍贵,虽然并不精致灵动,但保留了古代的朴素特征。
在这些“文化”中,方言是最外在、最鲜明、最有影响力的符号。
一个人一出生就听过这个方言,一岁就开始学了。他在发展认知能力、表达能力、思辨能力的过程中,一直依赖这种方言。所以,自然可以想象,这种方言对这个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一首关于母亲的歌,开头是这样的:“第一次听到,是你的呼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你的脸……”母亲用亲切的方言称呼儿子,当然;儿子看着母亲,当然看到的是在方言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淳朴面孔。第一次,是一个人生活来源的收敛。未来,即使命运掀起巨浪,每一滴水依然会包含最初的分子结构。在汹涌的水中舀一小勺味道,依然可以品尝到最初生活的“原味”。
“我是中国人!”这是国家的象征。
“我是太行山的!”这是该地区的标志。
中国——山西省——晋中市——一县——一村一镇……人就像一株植物。不管阳光下的花是饱满还是艳丽,它们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太阳在高高的天空中明亮地照耀着,阳光有益于田野,但根只深入一小块土壤。说到底,一个人的成长轨迹虽然不一样,但生命轨迹大致相同:从根开始,茎叶生长,经过光合作用,开花结果。深深埋在地下的根,总是为植物一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有句话说:“树移死,人移生。”人能动能活,并不是说人没有根,也不需要根,而是人作为万物的灵长类,远远优于普通植物,就是人可以带着根走路。人就像蒲公英的飞篷,随缘而飞,但无论落在哪里,无论环境和条件如何,他都不改变自己的特性,都会开出金色的花朵。
根在人心。
有专家学者考证,家乡方言属于晋语东山片。且不说“晋语”的范围很大,但这部“东山片”也涵盖了一市六县;然而,我的家乡话似乎仅限于方圆这一小范围的完全相同的发音。
家乡话的发音特点是:第一,发音很重,鼻子和背分不清,听起来有点倔;第二,语言的结尾升得很高,拖得很久,就像唱歌一样。当你听外国人说话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讶:这种语言将简单、收敛、轻盈与抒情结合在一起,真的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在长途汽车上讨论问题。两个人都脾气暴躁,说话很快,而且充满了方言。他们不断的来来往往,相互对抗,让我周围的乘客都惊呆了。话里带着隔阂,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你们是外国人吗?”
当然是白色的:“切!你是外国人!”
到目前为止,想起来还是没有心。
家乡话不仅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有丰富的古代文化。孩子晚上哭,大人经常吓唬说:“安静!你再哭,老马虎就来了!”小时候听到这种恐吓,就知道“老麻老虎”是个吓人的东西,可能会威胁到孩子的生命。那是什么?老虎?狼?不知道。直到大人们意识到所谓的“老马胡”其实是杨迪皇帝时主持运河发掘的“马树谋”。这个人留着胡子,所以乡亲们称之为“老马胡”。传说他爱吃婴儿肉,经常派人去偷民间婴儿吃,所以留下了这个方言典故来吓唬孩子。再比如,故里称不幸战败者为“不祥之兆”,这也有古代文化的渊源。这是傩文化占卜时代使用的术语。如果你在上帝面前画了一个倒霉的签名,你就倒霉了。所以我的家乡把倒霉的人叫做“不祥的亲笔”。
![[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 [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uploads/diyimg/oxaqpxyh97dgzz8189n2yej0ynb3d7.png)
方言里有神秘的东西:比如喜鹊是在树上筑巢的鸟,但老家叫“岩喜鹊”。也有历史原因造成的错误和失误。比如“酝酿”读作“热烈而忙碌”——主持人在农村开完会,会说:“你怎么看?下面熙熙攘攘,回头再给你出主意!”再比如“校对”,一般读作“校对(xiào)”——“把这个文档拿去校对(Xiào)校对!”这些词的拼写错误与方言无关,因为这些词刚引进的时候,先是被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念错,然后被群众传播,然后传播得太广,成为固定的念错,甚至成为“方言”。虽然年轻一代很清楚这些发音,但在这个古老的语言环境中,他们也采取从众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习惯”在方言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 [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uploads/diyimg/5fsxn43fg0o8gej16t5ra3q10ztx6i.png)
方言中也有一些迷信和地域歧视,不得不提。比如说,操不同口音的人,在老家就叫“毕”。起初,“比”是河北人的专用词。我的家乡与河北接壤,山西有煤,河北有小麦。由于资源配置,经济往来最多。但是,河北人强而诚,山西人弱。来到中国,山西人吃了很多苦,这就是所谓的“贸易逆差”。所以,当你听到别人叫“河北老头”的时候,总能从语气中想出点什么,有厌恶感。一个说:“骆驼不是动物,是人。”。山西老谢儿和河北老易是分不开的。他们一方面互相对立,一方面互相利用。
随着经济浪潮席卷全球,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随波逐流。他们以令山西人吃惊的韧性和耐力在艰苦的太行山扎下了根,他们拿走了山西人可怜的一勺饭碗。所以家乡人给了他们准确的分类:“四川彝,河南彝,东北彝,浙江彝,
唐代诗人何张之在一首诗中感慨地说:“离开家乡,家乡的声音不会改变。孩子们见面时,会笑着问客人从哪里来。”乍一看,这首诗轮廓清晰,精致而有味道,但里面却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它充满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只有在灰色的暮色中回顾生活时才能理解和表达的复杂情感。“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离开家。”诗人大半辈子都在外地度过,昔日的华严少年已成老人;“孩子不认识”,但带着熟悉的地方口音,诗人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我是这里人!
地方口音好听,难忘。家乡人对地方口音的感情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在家乡慵懒而古老的阳光中一寸一寸成长起来的,自然在日常生活的每一点点中得以维持。一个在斯里兰卡出生长大的人,无论是出国留学发展,还是仕途一路顺利晋升;不管你在外面说的是普通话还是外语,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你都需要毫无例外的融入古老的地方口音。是的,是发自内心的,超越情感需求的;没错,是由于周围文化环境的妥协:任何人回到家乡,说起南北口音,都会被邻居视为“假洋鬼子”、“走调”,甚至当地社会的社交圈也会拒绝你的进入。
不小心加入了一个qq群,里面全是家里的年轻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在深圳、上海、北京甚至大洋彼岸,在知识和文明的翅膀上“飞翔”,在那里编织自己的生活。他们远离了小时候被启蒙、被聪明的语言环境,却固执地依附于哺育他们的地方口音。因此,这个qq群成了大家了解乡音之痒的平台。群里的语音交流是一种方言,连对话框里的文字交流都煞费苦心地播放方言的原声。虽然从字面上看似乎不合理甚至有些古怪,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真的找不到发音相近的词,他们也不会同意,宁愿用汉语拼音代替。我的家乡话有很多变调和多模态助词。所以每当看到qq图标闪烁,顺手打开,屏幕上的短句都是用“李”“嗯”“哇”“门”“易”“美也”等助词修饰的。一股暖流突然流过我的心。
![[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 [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uploads/diyimg/fbmz4g240qkn0xnojmw5xpb1yr3kf1.png)
作家、歌手、企业家、从当地走出去的朋友经常和我通电话。当我谈到我的家乡时,需要两三个小时。有时我像小溪一样低语,有时我的情绪像洪流一样高涨。不难感受到这种语言的饕餮快感,仿佛看到他们在说话,牵手。大家都表达过这个意思:越是开心或者生气,就越想说家乡的方言。如果你不用方言来表达所有激动的情绪,你就不会到位和“无懈可击”!
我家乡的方言有这些忠心耿耿的人,尤其是被经济大潮刷新的年轻一代,他们被小心翼翼而又坚持不懈地维护和传承着,真的是当地文化的福音。现在是经济全球化,语言全球化的时代,说普通话,学外语是必须的。但是,在我看来,方言不应该消亡。作为一种文化,作为滋养自己特色文化的“根”,作为特殊地域特色和性格的依赖和支撑,我还是希望我的方言和世界上所有的方言都能很好的传承下去。俗话说“水土一方养人一方”。推而广之,不同的水土可以养出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人,从而使人多姿多彩、丰富有趣,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可以呈现出万千气象和无限美好。(孔瑞平)
标题:[文化]文化山西:方言里的文化
地址:http://www.huarenwang.vip/new/20181024/11.html
免责声明:山西时报网是一个向世界华人提供山西省本地资讯的门户网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山西新闻网将予以删除。
下一篇:[文化]文化山西:风华长城岁月歌